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前驻华记者冯哲芸(Emily Feng)2015年至2022年期间常驻中国。她在即将出版的新书《唯有红花绽放》(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中披露了这期间在逐渐收紧的社会控制中,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追索。以下是本台记者唐家婕、王允对冯哲芸的专访。
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担任大中华区记者近十年后,冯哲芸回到了华盛顿特区。她在中国的这些年,正值社会和经济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习近平巩固权力、“709”大抓捕、新疆再教育营、香港民主运动、美中贸易战、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以及国家向监控社会的转变。
最终,冯哲芸及其报道被卷入美中对抗的漩涡——她的签证遭到意外拒绝,被迫在驻外报道生涯的最后几年转往台湾。
她的新书《唯有红花绽放》是对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普通人个体身份认同与归属感的探寻。以下采访内容经过编辑,以确保篇幅与清晰度。
相关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RFA): 你在2015年22岁时移居中国。你当时最想探寻的问题是什么?找到了答案吗?
冯哲芸: 我想亲眼看看中国。我曾多次去中国南方探亲,但我对中国的变化充满好奇,尤其是在习近平执政的第三年。我想知道中国是否会继续开放——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我当时刚开始接触更多中文文化,也很好奇文化生产会如何演变。
我抵达中国的那天,正好是“709”大抓捕发生后一周。我当时还未意识到,那是中国政治的一次分水岭。这一事件深刻影响了我在接下来几年中所经历的中国。
RFA: “709”大抓捕震惊了许多人。它带来了哪些深远影响?
冯哲芸: 它影响了整个体系。许多具有影响力的律师被吊销执照——这些人曾在塑造中国法律与政治未来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不仅仅是个别人的遭遇,而是影响到了企业、组织乃至整个社会。
RFA: 你的书名《唯有红花绽放》是对毛泽东著名口号“百花齐放”的一种改写。你在书中写道,有人对你说:“这就是现在的国家。”能谈谈当时的情境吗?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这句话让你印象深刻?
冯哲芸: 书名体现了一种对立性。一方面,它是在赞美中国社会中本就存在的多样性——不同的声音、观点和身份认同,以及对私营经济、民族认同和普通话以外语言的不同看法。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国家正在日益试图压制这种多样性。
一位受访者对我说:“现在,国家只允许一种颜色的花盛开——红花。” 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我的书的主题:中国社会天然的多样性与国家控制之间的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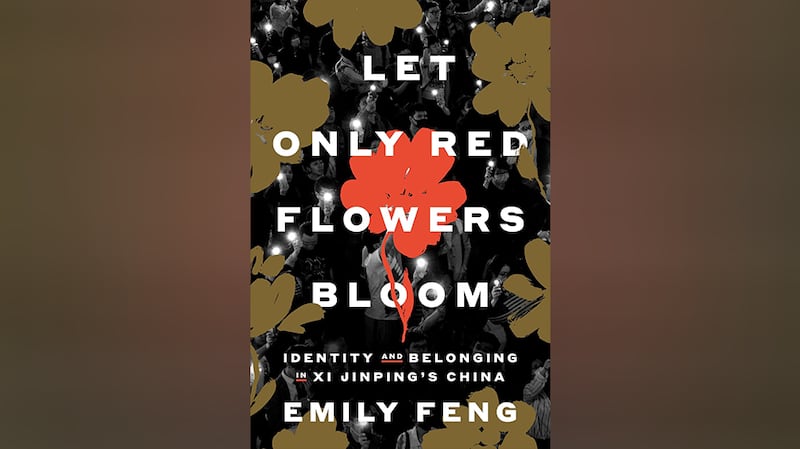
RFA: 你在中国报道了近十年,期间你观察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冯哲芸: 共产党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大大增强了。我刚到中国时,许多人对政治控制的感受相对较远。但随着时间推移,政府的干预逐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日常琐事。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严格的出行管控和监控变得更加明显。
我在报道中也能感受到这种变化。我刚到中国时,人们担心与记者交谈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受访者通常要求匿名以保护自己。但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网络上的监控愈发严密,人们的担忧也随之加剧。
尽管如此,我希望大家知道,中国依然有许多声音存在。即便在日益收紧的环境下,仍然有值得讲述的故事,我也希望更多的记者能继续在那里工作。
RFA:这期间有哪些重要时刻让你感觉社会控制在收紧?
冯哲芸:我开始想这个议题是因为新疆的这个问题。2017年的时候我开始报道新疆,然后当时只是听说有一些集中营。然后我一直跟踪这个故事以后,发现其实新疆这个议题、维吾尔族的这个议题对全国有很大的意义。它不只是西部的一个问题,涉及到当时的民族、政策、身份、语言、文化的这些个政策,同时也涉及到了中国和共产党对自己想创造什么样的国家的这样一个议题。所以从新疆这个角度,从这个切入点开始想到,身份为什么对中国当代的政治有那么核心的一个角色?
RFA:那么您作为一个外国记者,在报道中国的过程当中,你是否因为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而遇到过危险?
冯哲芸:是的。我因为报道而受到调查,我的新闻机构也因美中紧张关系而被审查。我多次不得不提前结束采访行程,有时甚至在采访过程中,受访者就被警方带走。我采访过的人可能会因此丢掉工作,甚至失去社会福利。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局面,但在中国做报道时,我必须时刻意识到这些风险。但我的经验中没有遇到什么意外,真的。
RFA:就算比较幸运的?
冯哲芸:当然我也受到一定的压力,但因为我有美国护照,然后我的新闻机构是美国的,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去做一些当地中国的记者没法做的一些故事。每次去报道的时候,我的态度就是也许这个是我的最后一个机会去报道在中国当地的一个故事,因为也许有一天我的签证没有了,或者我们这样自由去各种地方出差的机会会被剥夺。
RFA: 你如何与受访者建立信任?同时,你如何权衡对自己和他们的风险?
冯哲芸: 这需要每天去思考——和编辑讨论,和自己对话,更重要的是,和受访者沟通。我的许多报道并不是关于政府内部泄密,而是普通人的个人经历。建立信任意味着展现出我的倾听意愿,并努力与他们保持联系。
有时候,人们需要多年时间才能敞开心扉。例如,我采访过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直到他们真正消化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才愿意完整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所以其实我的失败率很高。在中国我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探索十个不同的故事,但是你只有20%、10%的机会才能成功。
RFA: 你的报道经常关注普通人的故事。在习近平的治理下,年轻一代如何面对身份认同的问题?
冯哲芸: 身份认同是我报道中最有趣的核心议题之一。中国一直在变化,每一代人都必须回答同样的问题: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
RFA:现在中国人很喜欢讨论中产阶层,他们很多人可能自以为就是中产阶层的一部分,那他们是如何讨论这种阶层身份的或者阶级身份的,尤其是在2018年开始经济下滑之后,他们中很多人是否越来越担心自己失去怎样的地位?
冯哲芸: 嗯,这个是好问题。我其实为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写了一篇报道,关于中产阶层的阶级意识。我刚搬到北京的时候,我还没感觉到大家很关注阶层这个身份。但是18年还是17年的时候,所谓低端人口的事情有很多,有很多流动人口的家被拆了。那时候我觉得人们就开始在大城市里面谈阶层这个议题。然后当经济下滑以后,人们的讨论就更多了。
RFA:你提到低端人口,其实是中国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口是属于他们叫做底层阶级或底层人口。我们在采访中其实接触很多这样的人,就是我感觉他们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媒,其实他们是严重被低估的,很容易被忽视的。那你接触的人当中,你觉得他们的意识形态是更左呢,还是更右?
冯哲芸:我觉得都有,都有。他们的看法会更极端,就会很偏左,或很偏右。我跟他们谈的时候就了解到,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生活背景太辛苦了,所以他们会觉得,哎,我很怀念毛泽东那个时代,当时那个政府还会照顾我们,或者他们会偏右,说我们应该用民主、有自由才能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RFA: 在管控日益收紧的时代,人们如何为自己争取个人空间或思想空间?
冯哲芸: 这变得越来越困难。我在书中采访的许多人,后来都离开了中国。一些人曾在体制内坚持了多年,甚至几十年。我讲述了一位前国家检察官的故事,她后来成为一名人权律师。她在体制内工作多年,最终选择走出体制,与其对抗。
很多人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直言不讳,什么时候需要保持低调。但我认为,连这种微小的灵活性如今也正在消失。事实上,在我完成书稿的初稿后,书中的大多数人物都已经离开了中国。
RFA:你在书中提到,理解中国政府它对自身的身份认定,以及他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公民,是理解中国的对外以及社会经济政策的关键。你可否举例,就是什么样的中国政策就体现了这样的官方身份?
冯哲芸:你看新疆的政策,就会显示出他们对身份的这个焦虑和重视。还有很多边界地方的这个民族和语言政策。但也可以看到,现在对这个红色教育的的重视。我刚搬到北京的时候,有很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东西在北京出现,这个就强调党的这个角色。
RFA: 外国记者在塑造全球对中国的认知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如今,驻华记者越来越少。对于那些从未去过中国的读者,你希望自己的报道能传递什么?
冯哲芸: 我希望人们能看到,归根结底,无论在哪个国家、说哪种语言,人性是相通的。对我而言,这本书也是个人化的。我父母出生在中国,我的家人至今仍在中国。我从未持有中国护照,但与这个地方有着深厚的联系。在中国生活时,我意识到自己以前所了解的中国,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是通过家人的视角、通过他们的移民故事来认识中国的。但中国有许多不同的面貌,具体取决于你在中国所处的位置和身份。
责编:安克; 网编:洪伟
